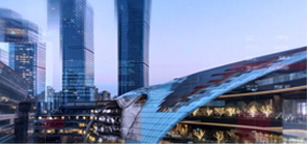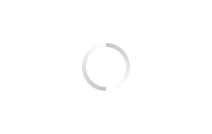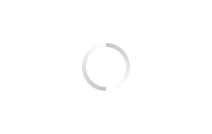
個人數據作為一種重要的、新的資產,越來越被視為當代經濟的基礎之一,對數據資產的控制似乎可以解釋科技巨頭公司為什么占據主導地位。蘋果、微軟、亞馬遜、谷歌和Facebook等美國科技公司市值龐大,他們的市場力量基于對個人數據的壟斷性控制,因此受到越來越多公眾的譴責,甚至形成了“科技抵制潮(techlash)”,但公司們仍然保持著優勢地位。本文分析了個人數據向資產的轉化,探索個人數據是如何被科技巨頭和其他政治經濟行為人(如投資者)核算、管理和評價。然而,本文的發現表明,科技巨頭通過對用戶指標(如用戶數量、用戶參與度)的執行性測量、治理和評估,將“用戶”和“用戶參與”變成了資產,而不是擴大對個人數據本身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本文將這一戰略概念化為“科技技藝(techcraft)”,關注科技巨頭如何利用方法和機制,使用戶和用戶數據成為可衡量和可識別的未來收入來源。
引言
數字化的個人數據經常被視為未來的資源,甚至是“新的資產類別”。在科技巨頭越來越有影響力的今天,個人數據的重要性十分顯著。正如Prainsack(2019)指出的,科技巨頭已經成為關鍵的社會和經濟中介,提供服務、產品和基礎設施,以換取我們的個人數據(Fourcade and Kluttz, 2020)。個人數據已經成為科技巨頭和其他數字技術公司的關鍵資產,為投資者評估未來收入和盈利預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新指標(Ciuriak, 2018; OECD, 2019; The Economist, 2020)。
隨著社會影響力的提升,科技巨頭越來越多地受到監管的關注。2020年10月,美國國會結束了對科技巨頭近兩年的調查,發布了關于“數字市場競爭”的報告。該報告強調,科技巨頭正在使用各種方式,利用其對數字生態系統和數據的控制來鞏固市場力量。之后不久,美國司法部宣布他們將起訴壟斷者谷歌違反反壟斷法。但即使出現了“科技抵制潮(techlash)”(Foroohar, 2019),輿論也沒有讓科技巨頭的估值下降;例如,它們的市值在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期間增長了52%,在一年內增加了近2萬億美元(The Economist, 2020:11)。投資者指望科技巨頭不斷積累更多的個人數據,從中獲得壟斷利益(e.g., Birch et al., 2020; Li et al., 2019; Mazzucato, 2018; Srnicek, 2016; Zuboff, 2019)。
科技巨頭及其投資者如何理解和構建個人數據?他們又是如何將個人數據作為資產進行管理和估值的?本文試圖分析這一問題,運用“資產化”概念以解釋科技巨頭的市場支配地位。資產化是一個在科技研究和政治經濟學領域發展起來的概念(Birch and Muniesa, 2020),強調了資源(如數據)向資本化財產的偶然轉變。本文將資產化理解為一種技術經濟秩序的模式,它有助于解釋政治經濟行為體所使用的測量、治理和評估實踐如何將個人數據轉化為未來的收入流。
個人數據的資產化
過去幾年關于資產化的文獻數量越來越多(Birch, 2017; Birch and Muniesa, 2020; Muniesa et al., 2017),包括之前關于個人健康數據資產化的研究(例如Beauvisage and Mellet, 2020; Birch et al., 2020; Geiger and Gross, 2021; Prainsack, 2020)。使用資產化的概念有助于本文理解科技巨頭如何將個人數據構建成新的資產類別。
個人數據可以被定義為“與已識別或可識別的自然人有關的任何信息”(Edwards,2018:81)。對個人數據的收集、使用和利用由來已久,然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數字化的個人數據是不同的,不僅僅是是其“數量、速度、種類和價值”與傳統數據不同(Prainsack,2019:1)。現在的數字化個人數據是通過數字流程收集的,這些流程能夠大規模收集和使用數據,并采用新的技術目標和收集結構以及新的使用邏輯(如推理預測等)(Cohen, 2019; Viljoen, 2020; Zuboff, 2019)。因此,大規模數字化個人數據涉及的算法具有固有的集體性質和網絡效應,例如,使用千萬級別的個人數據來預測個人或群體行為(Viljoen,2020)。個人數據被區分為“可識別的(identifiable)”、“匿名的(anonymous)”和“假名的(pseudonymous)”,其區別主要在于如何收集:可識別的是自愿的和知情的;匿名的是由數據處理者收集的,通常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所謂的匿名標識符收集得到;而假名的則是從第三方獲得。然而,從匿名和假名數據追蹤到個人的可識別數據的可能性越來越高(Edwards, 2018)。
Zuboff(2019:52)等學者將個人數據稱為“新的資產類別”,其中“每一次隨意的搜索、點贊和點擊都被視為一種資產”(ArvidssonandColleoni,2012;Pasquale,2015;Sadowski,2019)。其他學者試圖確定個人數據的法律意義,Lanier(2014)認為,個人數據應該由個人產權來管理,而Posner和Weyl(2019)認為,最好通過勞動關系來管理個人數據。但這些主張在目前還停留在法律討論層面:個人數據無法被擁有,因為姓名、地址、關系等信息是事實而不是創造性的產出(Cohen, 2019)。
在會計準則中,數字資源(如數據庫、軟件)和智力資源(如版權、專利、商標)被定義為無形資產(OECD, 2019)。國際會計準則(IAS)將無形資產定義為“無實物的可識別非貨幣資產”[IAS 38]。無形資產在衡量當代企業經濟業績方面的重要性不斷提高(Lev, 2019)。雖然將個人數據視為無形資產合乎邏輯,但它是否可以作為獨特的資源來衡量和估價,或者是否應該將其視為商譽的組成部分,在目前尚無定論。人們可以從市場反饋中解讀個人數據的價值,但這并不能說明分析個人數據是如何被科技巨頭衡量、管理或評價的。本文論點是,科技巨頭通過“科技技藝(techcraft)”使個人數據成為可衡量和可識別的資產,這個概念與Scott(1998)的“治國本領(statecraft)”概念相對應。首先,個人數據和無形資產一樣難以衡量。谷歌的首席經濟學家Hal Varian (2018)指出,只有已經出售或授權的數據才能被明確識別和衡量。因此,科技巨頭必須確定如何衡量數據。Fourcade和Healy(2017)借鑒了Scott(1998),認為數據價值的計算和衡量取決于對用戶的跟蹤和排名。同樣,Hwang(2020)認為,數字平臺和數字系統的技術架構使企業能夠將他們的用戶標準化,以便對他們進行測量。這樣的用戶指標和標準取決于技術手段。用戶度量和標準化依賴于科技技藝,它不僅包括指標和標準,也承載著壟斷和集中帶來的市場力量——對大公司而言,它們能夠將自己的指標作為行業甚至整個經濟的標準。
同樣,個人數據必須通過技術手段變得可讀和可測量,技術手段定義了“用戶”,將用戶作為可訪問的資源。科技公司通過獲得用戶的“注意力”或“印象”來盈利,并使用DAU或MAU等指標進行衡量。科技巨頭的權力來自于對用戶訪問的控制(Pistor, 2020),科技技藝則擴展了這種控制,例如,自動播放、持續滾動等(Kang and McAllister, 2011; Wu et al., 2020)。
最重要的,價值的衡量和識別以“用戶”為單位,而不是“個人數據”。用戶是對一個人使用系統的時間、積極性、規律性和重復性(即“參與”)的特殊衡量(Arvidsson and Colleoni, 2012)。而使用和參與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的標準化來衡量(Hwang, 2020)。用戶作為科技巨頭的指標被投資者所關注,可以解釋用戶如何或將如何被用來盈利。本文建立在Zuboff(2019: 129)的論點之上的,即科技巨頭正在通過調查和改變行為來制造“預測產品(prediction products)”,本文的論點是,科技技藝需要通過反復和表演性的行為,將用戶轉化為可測量和可識別的技術經濟對象,無論這種轉化是否真正讓個人行為變得可預測。
北美科技巨頭與科技抵制潮科技巨頭在北美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力日益增大。科技巨頭的崛起通常與數字平臺和系統的出現有關,它們在市場中連接買方和賣方,成為技術經濟的中介(Khan, 2017; Nieborg and Poell, 2018; Srnicek, 2016)。在這類市場中,大型企業和先行者有自我強化的優勢,網絡效應強化了“贏家通吃”的生態。大型網絡提供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這是由對數字化數據的控制實現的,以定制服務、回應、預測和創造需求(Khan, 2017)。監管缺失與網絡效應結合,形成了自然壟斷,科技巨頭作為線上市場的制造者,利用其規模和對數據的控制,成為了市場基礎設施的參與者。科技巨頭往往愿意接受中短期的低收益,其長期目標是通過未來對數據的控制來爭取市場和形成壟斷(Foroohar, 2019; Khan, 2017)。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科技巨頭逐漸成為熱門的投資選擇,融資反過來使科技巨頭更有可能超越資金不足的競爭對手(Galloway, 2018; Srnicek, 2016)。如圖1所示,2020年中期,科技巨頭的市值已經達到標準普爾500指數覆蓋的所有公司的總市值的近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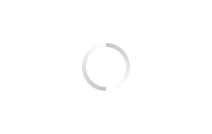
圖1科技抵制潮起源于公眾和政策對科技巨頭信任的瓦解,這一傾向始于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Foroohar, 2019),并因2018年劍橋分析公司和Facebook濫用數據而加劇(Zuboff, 2019)。公眾輿論逐漸推動政策和政治的調整,個人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受到了更多的監管。在美國,科技巨頭成為反壟斷改革的焦點(Crane, 2018)。這一浪潮也讓北美現有反壟斷立法的裂痕得以暴露(Crane,2018; Khan,2017)。消費者福利原則默認只有在對消費者產生負面的實質性影響(即短期價格上漲)時壟斷問題才變得重要,但這忽視了科技巨頭通過控制數據積累的結構性市場力量(Khan, 2017)。科技抵制潮似乎并沒有影響到科技巨頭的發展。
研究方法
個人數據作為未來數字經濟的關鍵資源,有望成為資本積累的新手段(Sadowski,2019)。本文希望通過上文介紹的科技技藝概念,了解科技巨頭和其他政治經濟行為體如何理解、管理和重視個人數據。研究者經常用“GAFAM”來稱呼目前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五家科技公司,即蘋果、亞馬遜、Facebook、谷歌(即Alphabet)和微軟,由于本文感興趣的是那些主導個人數據收集的科技巨頭,所以在此選擇GAFAM成員作為分析對象。本文結合多種研究方法,包括對決策者的定性訪談、Compustat的財務數據、Seeking Alpha數據庫中的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以及科技巨頭的年度報告。
在2019年和2020年,作者采訪了美國和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第二,作者從Compustat收集了大量財務數據,比較了科技巨頭和美國前200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和資本化程度(即債務加股權)。最后,作者收集并分析了科技巨頭的財報匯報資料(2010-2019年)和財務報告中的信息,以分析投資者和科技巨頭如何在報告中理解、管理和衡量個人數據。
采取混合方法的理由有兩個方面。首先,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出臺的《通用會計準則》目前不允許將數字化個人數據作為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其次,如果個人數據沒有出現在大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作者希望通過檢查公司的電話會議和財務報告來研究哪些數據(例如用戶指標)關系到公司的運營、收入和利潤。由于財務披露對股東的重要性,數據的測量、治理和估值可能會在這些材料中得到定性反映。
科技巨頭如何衡量、管理和評價數字數據?
公司的資產基礎是以市值為標準的。本文旨在研究個人數據如何被科技公司和其他市場參與者所衡量。如上所述,雖然個人數據不能直接作為資產入賬,但可以獲得隱性的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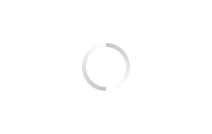
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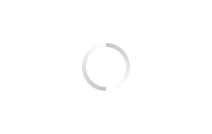
圖3
首先,作者嘗試衡量科技巨頭所持有的個人數據。圖2顯示了美國前200名公司的資產基礎,可以看出,1950年至2020年期間財產、廠房和設備(固定資產)的大幅下降和無形資產的上升。圖3反映了“GAFAM”五家科技巨頭的資產占比情況,其中隱含的是,部分無形資產的增長可以歸因于個人數據。然而個人數據的市場價值和會計價值之間存在著混淆,后者是不可識別的,而前者是根據無形資產的擴張推算出來的。無形資產的實際價值超過了資產負債表上記錄的內容。
圖3還反映了科技巨頭對資產劃分的差異。這些統計差異源于其資產結構和會計的不同(Birch and Muniesa, 2020)。而且盡管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了披露要求,但公司仍保留有很大的自由度。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8年蘋果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無形資產分類的消失。
盡管科技巨頭之間存在異質性,但科技巨頭與市值前200名中的其他公司存在著更明顯的區別。亞馬遜、谷歌和Facebook與200強企業中固定資產份額穩定、無形資產份額增長的趨勢背道而馳。自上市以來,這三家公司的資產基礎中有形資產的份額都增加了不止一倍。甚至截至2019年,谷歌和Facebook的有形資產占比都略高于200強企業的平均值。200強企業的無形資產平均約占30%,但亞馬遜和谷歌的無形資產占其資產的比例不到10%。這一矛盾要求研究者必須首先理清科技巨頭的估值的模糊性。
個人數據是一種無形資產嗎?個人數據既不能作為獨立的無形資產,也不能作為商譽來計算(Laney, 2018)。Varian(2018)認為,由于個人數據本身不能被擁有,因此科技巨頭收集的個人數據的訪問權可能成為一種資產。
為了了解科技巨頭是如何管理個人數據的,本文分析了管理人員、財務人員(如分析師、投資者)的季度財報電話會議。通常情況下,財報電話會議主要由公司高管(如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構成,然后是涉及財務業績和未來計劃的問答環節。如果個人數據被視為科技巨頭的重要資產,那么可以預計有關信息會被詢問到,然而,作者對電話會議的分析表明,幾乎沒有利益相關者對個人數據本身表示興趣。表1顯示了作者對這些財報電話會議進行的定量文本分析,它顯示,在五個大型科技公司近十年的財報電話中,“個人數據”只被提及兩次,分析師們最關心的不是個人數據,而是“貨幣化(monetization)”,而貨幣化的首選技術-經濟對象就是“用戶”(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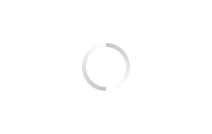
表1
科技巨頭具有異質性,但對用戶的關注不僅與那些依賴于廣告的公司(如谷歌、Facebook和現在的亞馬遜)有關,而且也與蘋果和微軟等公司有關。例如,從2015年第一季度財報電話會議開始,蘋果公司高管一直將設備的活躍使用者稱為其“installedbase”,并在“設備安裝量(installed base of devices)”和“用戶安裝量(installed base of users)”的使用之間搖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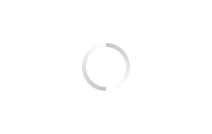
圖4
科技抵制潮之后的隱私問題同樣重要(Foroohar, 2019),圖4體現了不同時期公司們對“隱私”提及的情況。2018年之前,財報電話會議中對隱私的討論較為有限,但在2018年和2019年,人們對隱私的關注度大幅躍升。在Facebook的2018Q2問答中,花旗集團的一位分析師問道,“讓人們對自己的隱私和數據有更多控制權”是否會對Facebook的收益產生負面影響,高管的回應肯定了這一影響的存在。
科技巨頭在處理個人數據時存在不同。當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分析師問及蘋果公司對隱私保護的主張時,庫克回答:“如果你了解我們的模式、我們能說服你購買iPhone或iPad,我們就能賺錢。你不是我們的產品。”換句話說,更多的隱私保護并不會傷害蘋果公司。
正如這些經驗材料所表明的,用戶被理解為資產,前提是用戶數據和“生態系統(ecosystems)”的貨幣化。科技巨頭無法直接把個人數據作為一種資產來擁有,而資產化涉及:(1)部署標準、數字架構,以衡量和劃分用戶和使用情況;(2)系統內的用戶配置;(3)為不同的目的(如:培訓算法、數據分析、數據處理),對用戶和使用情況指標進行合約的(通過服務條款)和技術(通過互操作性)的限制;(4)從不同的貨幣化機制中獲得未來收入,包括用戶在系統內的留存(如蘋果),提供訂閱服務(如微軟),出售對用戶和用戶數據的訪問權(如Facebook、谷歌),或對平臺的使用收取一系列費用(如亞馬遜)(Arvidsson and Colleoni, 2012; Cohen, 2019; Wu et al., 2020; Zuboff, 2019)。
因此,科技巨頭通過 "數據化設計的人工制品"(Cohen, 2017: 160)部署技術手段,將個人數據轉化為用戶指標;這些人工制品被設計和配置為吸引注意力,產生活動,并刺激進一步的相互行動,產生更多關于用戶的數據(Arvidsson和Calleoni, 2012; Kang和McAllister, 2011; Wu等人, 2020; Zuboff, 2019)。在這里,"用戶"、"使用 "和 "對用戶的訪問 "最終成為可識別的技術經濟對象,科技巨頭可以通過不同的貨幣化戰略將其視為未來的收入來源。
根據資料,從2010年到2019年,科技巨頭平均花費了230億美元的現金用于收購,遠遠超過市值前200名公司收購花費的平均值84億美元。根據Wichowski(2020: 63–64),科技巨頭公司在1998年至2018年期間進行了1227項投資或收購。鑒于其異質的商業模式,科技巨頭在收購方面存在差異,但其商業模式的核心共性是他們都在加強對用戶、用戶參與和用戶訪問的壟斷。
在收購支出方面處于較低水平的是Facebook,在過去10年中現金支出為75億美元,最大一筆發生在2014年,當時Facebook以46億美元的現金和150億美元的股份收購了WhatsApp。兩年前,Facebook以10億美元收購了Instagram,特別是因為Instagram的“用戶參與度”(不只是用戶數量)已經超過了其他社交媒體網站(Galloway, 2018)。值得注意的是,該交易中的“商譽”的價值為4.35億美元,這份報告中沒有提到個人數據,但“用戶參與”卻被提及15次。
收購支出較多的企業是微軟,過去十年微軟在收購上花費了522億美元,包括2017年主要用于收購LinkedIn的259億美元。微軟的收購步伐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它的無形資產占比不斷增長。微軟在2017年10-K報告中闡述了,收購LinkedIn有望再次提高用戶參與度。
根據目前的會計規則,個人數據的價值可能會在“商譽”的估值中顯示出來。自21世紀初以來,商譽在200強企業的無形資產中占到60%左右。然而,對于大型科技公司來說,商譽占到了無形價值的80%。在本文研究的年度報告中,大型科技公司并沒有將個人數據作為商譽的一部分來評估;相反,用戶參與和“協同效應”構成了商譽。而且公司和用戶之間合同性質的措施(如條款)非常重要,因為這些條款本身可以和公司分離(Lev, 2019)。
同樣,本文發現,科技巨頭并不重視個人數據本身,相反,公司通過跟蹤和記錄用戶在系統中的參與度來評估用戶和用戶指標(Fourcade and Healy, 2017)。在這里,techcraft是基于用戶數量、用戶參與度、用戶點擊率、點擊率等對用戶數據的具體估值,收購只是這一商業化手段的縮影之一,(Lubian and Esteves, 2017);通過用戶簽署的授權協議、通過技術捕獲,公司獲得對用戶數據的訪問(Pistor, 2019)。用戶參與的價值則在于,它帶來了重復的收入流,而不是一次性收入,進而推動了訂閱制商業模式的傳播(Perzanowski and Schultz, 2016; Sadowski, 2020)。尤其重要的是,用戶在條款和合約中無限期地授權,而這些條款和條件可以被科技巨頭隨意修改(Obar and Oeldorf-Hirsch, 2020),眾多應用程序中嵌入的第三方權限條約還間接獲得了關于用戶的朋友或家人的信息(Lai and Flensburg, 2020)。Fourcade和Kluttz (2020: 6)稱之為“莫斯式的交換”,所謂的互惠交換實際上“將用戶鎖定在不斷更新的交易循環中,在這個循環中同意的期限被假定為‘永遠’”。
2020年美國國會聽證會的報告列出了科技巨頭為控制用戶訪問權而部署的各種技術經濟機制,例如,Facebook“根據它是否將其他公司視為競爭威脅,有選擇地執行其平臺政策”(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20: 166),谷歌向蘋果公司支付大量資金,以確保iOS設備使用其產品搜索,從而擴大其用戶群。用戶數量已經成為科技巨頭權力的衡量標準。
DAU、MAU或用戶群的衡量標準是這些公司及其投資者的關鍵指標。用戶并不是產品,因為用戶沒有被出售;相反,他們是個人數據的新資產類別,可以產生持續的收入流。“用戶”是技術經濟對象,通過一系列技術和社會法律選擇(如合同權利、對相互操作性的技術限制)構成的,這些選擇塑造、限制了數字平臺或生態系統內的活動,從而使用戶成為可識別和可衡量的經濟信號(Fourcade and Healy, 2017; Scott, 1998; Wu et al., 2020)。
在這里,“使用”很重要,用戶必須以特定的技術經濟方式參與數字技術,科技巨頭則對常規用戶參與度加以關注,以“每用戶帶來的平均收入”衡量。因此,并不是個人數據本身變成了一種資產,而是技術手段使用戶和用戶參與成為可識別和可衡量的資產,這種方式最終加強和延續了大公司獲得的市場力量。
結論與討論
已有學術、政策研究認為,個人數據是科技巨頭持有的寶貴資源或資產,這是數據壟斷相關研究的前提之一,而本文表明,與最初前提相反,個人數據并沒有被納入科技巨頭的資產負債表。因此,作者探討了科技巨頭的治理和評估做法,發現科技巨頭通過使用戶和用戶參與變得可衡量、可識別和可用于盈利,將個人數據資產化。隨著科技巨頭對用戶數據的收集增加,他們還可以修改使用條款及合約以增加利益所得。因此,科技巨頭使用科技技藝,創造了一種遞歸的結果:用戶被(重新)配置為技術經濟對象,而數據壟斷則使對用戶的技術經濟配置成為可能。科技巨頭的力量體現在用戶資產化的過程中,而不是來自個人數據的“所有權”。
(部分內容來源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